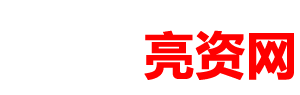亦慈亦让沈从文,亦慈亦让沈从文答案
网友投稿 2023-07-17 10:09:51亦慈亦让沈从文一见钟情,两人很快坠入爱河。张兆和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子,她不喜欢浪漫,更不喜欢出去玩,但是沈从文却不一样,他对张兆和的爱是烈的,他愿意为了张兆和放弃自己的事业,在家里做一个贤妻良母。张兆和也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女子,她对沈从文的爱也是深沉的,她不不喜欢别人说她的丈夫是一个 *** ,所以她从来不在外人面前提起他。
一:亦慈亦让沈从文答案
19.(2分)沈从文先生一生的创作源泉和文学基础主要来自“凤凰城内外那本由自然和人事写成的社会大书”。20.(3分)“照我(我;或者作者;或者沈从文)思索,能理解‘我’(你;或者与“我”相对的个体;或者读者);照我思索,可认识人(他;或者社会中人;或者他人;或者人们)。” 21.(3分)沈从文先生的文章如日月星斗光被人间,洗从文先生的人品亦慈亦让令人如坐春风,他是我国近代史上不可多得的德艺双馨的文学大师。所以,能够“长久地受到人们的敬仰”。(凡是能扣住文学创作方面的崇高地位,突出“星斗”之意和表现不求名利,谦逊让人的品格两方面来回答的,均可得分。内容有缺失和表达不准确的相应扣分。)
22.(2分)创作题材:作品主要以湘西生活为题材,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、自然的生命形式,赞美人性美。(只答前半句的亦可。)
创作主题:主要凸现了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,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。(只答后半句的亦可。)
23.(2分)苟全性命于乱世,不求闻达于诸侯。(错一字扣1分)
1、沈从文先生一生的创作源泉和文学基础主要来自“凤凰城内外那本由自然和人事写成的社会大书”。
2、“照我(我;或者作者;或者沈从文)思索,能理解‘我’(你;或者与“我”相对的个体;或者读者);照我思索,可认识人(他;或者社会中人;或者他人;或者人们)。”
3、沈从文先生的文章如日月星斗光被人间,洗从文先生的人品亦慈亦让令人如坐春风,他是我国近代史上不可多得的德艺双馨的文学大师。所以,能够“长久地受到人们的敬仰”。
4、创作题材:作品主要以湘西生活为题材,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、自然的生命形式,赞美人性美。 创作主题:主要凸现了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,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。
5、苟全性命于乱世,不求闻达于诸侯。
二:亦慈亦让沈从文阅读答案
1、沈从文先生一生的创作源泉和文学基础主要来自“凤凰城内外那本由自然和人事写成的社会大书”。
2、“照我(我;或者
3、沈从文先生的文章如日月星斗光被人间,洗从文先生的人品亦慈亦让令人如坐春风,他是我国近代史上不可多得的德艺双馨的文学大师。所以,能够“长久地受到人们的敬仰”。
4、创作题材:作品主要以湘西生活为题材,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、自然的生命形式,赞美人性美。 创作主题:主要凸现了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,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。
5、苟全性命于乱世,不求闻达于诸侯。
三:亦慈亦让沈从文文章开头的环境描写有什么作用
【追光文学巨匠·纪念沈从文诞辰120周年】
今年是沈从文诞辰120周年。对他这个人和他的文学、文化实践的基本理解,需要从孤立的、稳固的、规定性比较强的观念中摆脱出来,在更广阔的时空里,特别是在他与置身其中的20世纪中国的持续性动态关系中,展开讨论。事实上,沈从文的自我、文学、后半生践行的物质文化史研究,也正是和时代不间断的对话过程及其结果。
沈从文(1902—1988)资料图片
通过对以往所有生命经验的积累、扩大和化合来确立“自我”
沈从文的墓碑是一块大石头,正面刻着他这样两句话:“照我思索,能理解‘我’。照我思索,可认识‘人’。”
那么,“照我思索”的“我”是怎么回事?
在20世纪的中国,有一种典型的——因为普遍而显得典型——关于自我的叙述,就是在生命经验的过程中,猝然遭遇到某种转折性的震惊时刻,因而“觉醒”。这种“觉醒”是“现代”的“觉醒”,因为造成“觉醒”的力量,直接或间接地来自现代思想和现代理论。“觉醒”以前糊里糊涂,蒙昧混沌不成形,“觉醒”之后恍然大悟,焕然新生。这种类型的叙述很多,已经成为一种经典模式,不单单是一种文学模式,同时是更为广阔的现代文化和现代社会的一种叙述模式。
这没有什么奇怪。个人的震惊性经验是和古老中国的“觉醒”共振而生的,社会的现代转型和个人的现代塑形互为因果,互相呼应。从单个人的角度来看,这个现代的“我”似乎主要是由现代思想和现代理论所促生和塑造的,它的根源不在生命本身,而是外来的力量。
但是,这种断裂式的“觉醒”没有发生在沈从文身上。他的“我”,不是抛弃“旧我”后新生的“新我”,而是以往所有的生命经验一点儿一点儿积累、扩大、化合而来的,到了一定程度,就可以确立起来。这样确立起来的自我,有根源,有历史。从这个意义上看《从文自传》,就会发现这本书不仅好玩、有趣,而且或显或隐地包含了理解沈从文这个人和他全部作品的基本信息。
“我”是从哪里来的?“我”是怎么来的?生命的来路历历在目。自传写到21岁离开湘西闯进北京即戛然而止,自我的形象已经清晰地确立起来了。可以说,正是借助自传的写作,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确认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,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,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明朗起来。过往的经验和历程之所以有意义,之所以要叙述和值得叙述,就是因为要靠这个过程才能把自我确立起来。在这里,可以看到一个基本的不同,断裂式“觉醒”的“新我”是靠否定自己的历史而确立的,而沈从文的自我是通过肯定自己的历史而确立的。
1984年第8期《大众电影》封面刊发电影《边城》剧照资料图片
之所以要确立这样一个自我,对于一个年轻的写
对于更加漫长的人生来说,自我确立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学上的;这个确立的自我,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和挑战,要去经历多重的困惑和艰难的重生,而且要在生命的终结处,获得圆满。
不是说沈从文确立了自我,这个自我就固定住了,因为实感经验在时时增加,生命的来路在刻刻延长,新的问题层出不穷,也会激发出对自我的新的询问和新的发现。
每到大的关口,沈从文会习惯性地勘探自我的来路,以此帮助辨认现在的位置,确定将来的走向。《从文自传》写在创作的巅峰状态即将出现的前夕,仿佛是对沈从文最好作品的召唤;《从现实学习》于纷纷扰扰的争斗中强调个人在时代里切身的痛感,对自己的文学未来及早作出预言;在孤立无援的时候,他又写过两篇自传,一篇叫《一个人的自白》,另一篇叫《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》,有心的读者通过这种特殊的写作,能够对沈从文其人其作产生更为深切的感受和贴近的理解。
带着实感经验的历史和累积的感情来看人看世界
新文学对“人”的重新“发现”,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启蒙紧密纠缠在一起的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物,农民、士兵、水手,如果放进一个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学叙事模式里,大多应该处在被启蒙的位置。但沈从文没有跟从这个模式。他作品的叙述者,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较起来,并没有处在优越的位置上,相反,这个叙述者却常常从他们身上受到“感动”和“教育”。而沈从文作品的叙述者,常常又是与
当这些人出现在沈从文笔下的时候,他们不是作为愚昧落后中国的代表和象征而无言地承受着“现代性”的批判,他们是以未经“现代”洗礼的面貌,呈现着他们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。沈从文对这些人“有情”,他能从他们身上体会到生命的努力和生存的庄严,体会到对人生的忠实与对命运的承担。
沈从文是一个把根扎在自己实感经验中的人,并且带着实感经验的历史和累积的感情来看人、看世界。他的一句话,经当年的学生汪曾祺转述后,成了常被引用的写作名言:“要贴到人物来写。”看起来是说写作 *** ,其实牵扯更重要的问题:怎么才能“贴到人物”?没有切身的感情,不能从心底里自然而然地生出亲近感、亲切感,是贴不上的。从根本上说,这不是 *** 的事,而是心的事,能不能贴到人物,取决于有没有一颗对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普通人贴近的、“有情”的心。
沈从文的文学过去了这么多年,为什么还有蓬蓬勃勃的生命力?单从他作品里的人物来说,是他没有把这些人物放到框子里,没有用这种或那种理论的彩笔去给他们涂颜色,没有自以为可以给他们定性,没有把他们变成符号。他们有生机,是生命自身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生机。而且,沈从文并不因为自己对这些人物非常熟悉就自负能够“把握”他们,他给张兆和的信里说:他来写他们,“一定写得很好。但我总还嫌力量不及,因为本来这些人就太大了”。“太大了”,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感受——他坚信生活中的人都是饱满的存在。有不少作家自以为可以“把握”他笔下的人物,就是因为他没有生命“太大了”的感受,他把他们限制、规范在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感受能力之内,当然就“把握”得住了。
晚年的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资料图片
作品看起来精致纤巧,却蕴藏着一个大的世界的丰富信息
沈从文的文学世界,不止是人的世界,而且要比人的世界大。简单地说,沈从文的文学里面有天地,人活在天地之间。现代以来的大部分文学,只有人世,人活在人和人之间,活在社会关系的总和里面。
“天地”这个概念,和自然相通,但不是自然;和人事相关,却高于人事。读沈从文的文学,如果感受不到“天地”,会读不明白。譬如说《边城》这篇传播广泛的作品,里面有些非常重要的东西,没有这种感受,就无法透彻理解
在这里顺便说几句沈从文的景物描写。沈从文作品中的景物,通的是自然,自然又通天地,一层一层往上,所以有无限生机。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景物,是图像化了的东西,是我们的眼睛或者相机截取了的片段;即使我们能够通过片段的景物联想到自然,那也是近代以来我们所理解的自然,是被我们对象化的东西,我们把人当成主体,把自然当成主体的对象。我们虽然欣赏和赞叹沈从文的景物描写之美,却不容易领会他的自然观中与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相连的天地大美,与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相连的天地大德,当然也就更不容易理解与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”相连的天地不仁。天道、地道、人道。人道仅居其间,我们只承认人道,只在人道中看问题,只从人道看自然,自然也就被割裂和缩小为人的对象了。但其实,天地运行不息,山河浩浩荡荡,沈从文的作品看起来精致纤巧,却蕴藏着一个大的世界的丰富信息,自然在他的作品中,岂止是这样那样的景物描写?
我还想借这个话题说一个词:人性。很多人谈论沈从文作品,喜欢用这个词。沈从文自己也用这个词。我想提醒的是,沈从文是在一个比人大的世界里说人性的,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论的人性不同,和我们通常在人的世界里说人性不同。他感受里的人性,包含着与人居其间的天地运行相通的信息。
《光明日报》上的沈从文足迹
● 1954年10月3日,刊发沈从文的文章《略谈考证工作必须文献与实物相结合》,文章写道,新的文史研究,如不更广泛一些和有关问题联系,只孤立用文字证文字,是路走不通的。几首古诗的注,还牵涉许多现实问题,何况写文学史,写文化史?朋友传说北京图书馆的藏书,新中国成立后已超过五百万卷,这是我们可以自豪的一面。可是试从图书中看看,搞中古雕刻美术问题的著作,他国人越俎代庖的,云冈部分就已出书到二十大本,我们自己却几个像样的小册子也还没有,这实在格外值得深深警惕!这五百万卷书若没有人善于用它和地下挖出来的,或始终在地面保存的百十万种不同的东西结合起来,真的历史科学是建立不起来的!
● 1962年5月26日,刊发沈从文的文章《题〈寄庑图〉后》,文章写道,(个石)先生虽久绾县事,却无丝毫官气,还是一切依旧,言行敦实如老农,心境则旷达明朗,除读书养志,日常惟循湖作诗。积德聚学,益臻纯粹。每一接谈,总能给人一种亲切感印,深一层体会到古代学人所谓“反璞存真”意思。三十年来时移世易,家乡亲故无论老成少壮,秋风黄叶,凋落垂尽。惟先生年近古稀,体力思想均尚健全,仁者必寿,百岁可期。
● 1980年11月7日,刊发报道《坚实地站在中华大地上——访著名老作家沈从文》,其中写道,沈老前年得了脑血栓病,住过两次医院,今年春节前才出院,现在还不能多讲话。沈夫人张兆和老人只好谨遵医嘱,在门口贴了张用毛笔工工整整写的字条“沈老有病,谢绝会客”。沈夫人笑着说:这个谢贴,对老朋友都不适用。今年春天,巴金从上海到北京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,巴老身体不好,一般活动都不参加,就要来看沈老。八十多岁的人了,让女儿扶着,爬上五楼,在楼梯上还摔了一跤。沈老十分过意不去,巴老却说:“这是我心甘情愿的,摔了一跤也乐意。”
● 1988年5月17日,刊发简讯《一代名作家沈从文逝世》,报道指出,中国著名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沈从文先生,因病于5月10日晚8时35分在北京逝世,享年86岁。
● 1988年5月29日,刊发沈从文的遗作《自我评述》,其中写道,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,始终还是个乡下人,不习惯城市生活,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,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。虽然也写都市生活,写城市各阶层人,但对我自己作品,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。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。
● 1993年11月16日,刊发报道《〈沈从文全集〉出版签约》,报道指出,全书共20余卷,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系首次发表,而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这部皇皇巨著,亦将首次与大陆读者见面。
● 2014年8月29日,刊发张新颖的文章《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——记沈从文最后的岁月》,文章写道,自从1983年病倒之后,沈从文行动不能自如,说话也越来越少,越来越简单,流泪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。为自己伤感,对他人同情,被艺术感动,还有更为复杂交织在一起的感情,都有可能令他不能自已。外人看来突然的反应,在他自己却是自然;家里人也在逐渐变化的过程中理解。
● 2018年5月14日,刊发徐兆寿的文章《从沈从文身上找寻诗意的世界》,文章写道,沈从文平静如水,温润如玉,但又坚韧不拔。他是藏在深山里的竹子,自有气象。他仿佛是宁静的湖泊,幸福的炊烟,虽有因为人生的种种不得已而生出的淡淡的哀伤,但也理解天地世情,不破那东方的气韵,以此向他的读者展示一个从古代留传下来的诗意中国。
《光明日报》( 2022年08月17日14版)

热门文章
-
 安徽办理资金证明(安徽代办存款证明所需材
2023-06-22
安徽办理资金证明(安徽代办存款证明所需材
2023-06-22
-
 张掖办理资金证明(张掖代办存款证明所需材
2023-06-22
张掖办理资金证明(张掖代办存款证明所需材
2023-06-22
-
 阳江工程亮资_阳江亮资摆账公司
2023-04-08
阳江工程亮资_阳江亮资摆账公司
2023-04-08
-
 专利评估收费标准
2023-02-17
专利评估收费标准
2023-02-17
-
 福建办理资金证明(福建代办存款证明所需材
2023-06-21
福建办理资金证明(福建代办存款证明所需材
2023-06-21
-
 年金现值系数表
2022-12-26
年金现值系数表
2022-12-26
-
 肇庆办理资金证明(肇庆代办存款证明所需材
2023-06-23
肇庆办理资金证明(肇庆代办存款证明所需材
2023-06-23
-
 嘉兴办理资金证明(嘉兴代办存款证明所需材
2023-06-22
嘉兴办理资金证明(嘉兴代办存款证明所需材
2023-06-22
-
 衢州工程亮资_衢州亮资摆账公司
2023-04-06
衢州工程亮资_衢州亮资摆账公司
2023-04-06
-
 零首付无息贷款买车可靠吗?怎么办理?
2023-02-27
零首付无息贷款买车可靠吗?怎么办理?
2023-02-27